原文標題:Unintended Architecture
作者:Meltem Demirors 譯者:Frau Yang 翻譯機構:DAOSquare
我願即我造,我造即我
最近,我每次都花一點點時間,一直在探索紐約的另一面,這個我在過去六年裡稱之為家的城市。當你看到一座空無一人的城市,你開始明白建築的重要性。你會看到城市的骨架,你開始明白是什麼讓人流有了形狀、節奏和能量。
你看,我們的設想變成了我們的建造物。我們所建造的東西又體現在我們的體驗中。這一點在物理空間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現在,許多每天24小時都呆在家裡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體會到這一點。但更重要的是,當你建造一些東西時,它不僅僅影響你自己,它還影響著你周圍的一切,它轉移和重新引導人群、思想、原子和星塵的流動。
當我們研究古代文明時,我們常常依靠建築來推斷我們的祖先如何生活。

土耳其Göbekli Tepe的照片,來源於thetravel.com
我們的祖先重視什麼,他們崇拜什麼,他們擁有什麼技術,他們擁有什麼知識,他們與自己和彼此的關係,以及與自然和神靈的關係,我們可以從這些開始了解。
但這也發生在數字空間,以及精神和文化空間。我們建造的東西會成為我們,而我們是什麼,又影響著我們的建築。
建築決定形式
設計是一種普遍的語言,它超越了空間和時間。我們從形式中推導出功能。
建築師為社會體驗設計空間。作為一門學科,建築學將物理學、數學和材料科學的嚴格規則與藝術、設計、哲學和社會學的流動性和自由性相結合。
這就是我喜歡建築的原因——它揭示了許多和我們世界的狀態相關的事。它揭示了我們的能力,我們的意圖,我們的慾望。它改變了我們的心情,我們的心理,我們的行動和生活方式。
我們進行建造的方式對我們如何體驗周圍世界有著深遠的影響。如果我們建造的東西是開放和包容的,我們就會支持這樣的想法,認為我們是一個集體的。如果我們建造的東西是排斥性的,能夠區分人群的,我們就會延續這樣的觀點,覺得我們是獨立的部落和群體。
換句話說,借用普利茲克獎(有建築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說法:社會產生了建築,而建築,雖然沒有產生社會,但卻幫助維持了許多社會形式。
這些固定性與流動性之間的界限,在限制性與表現性之間的界限,它們可以是物理性的,比如牆,但也可以是技術性的、政治性的、情感性的和精神性的。
我們正在經歷的當下,正在塑造我們對未來的渴望。也許你已經註意到了你對空間的感受,對特定類型空間的渴望,以及對更廣闊和更開放的空間的渴望。渴望與更多的同理心、耐心和同情心建立更深層次的聯繫。從交易關係到情感關係的轉變,一個開放的交流和表達的論壇,或者從更正式的預定對話轉變為更隨意的非結構化的論壇討論。
新建築師:數字空間的新領域
我們體驗世界的方式不再僅僅由我們居住的物理空間決定。我們的交流、交易和運動的邊界由我們周圍的數字基礎設施所決定。隨著新平台、新媒介和新工具的大量湧現,我們已經為藝術、技術、金融、設計、知識、交流等建立了新的操作系統。
想一想更微妙的建築,它正在驅動你的行為,驅動你的情緒,驅動你的信念。你正在閱讀這一頁,但你是如何來到這裡的?在你到達之前,你究竟知道你想來這裡嗎?還是你不顧自己,風塵僕僕地來到這裡?
新的建築師塑造了你在數字世界中的生活,控制著你觀看周圍風景的光圈寬度,在你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模糊和轉移焦點。他們還塑造了你的慾望,你的報復,你的夢想,你的努力,你的精力,以及你寶貴的時間。
他們正在搭建基礎設施和界面,讓你能夠導航、搜索、溝通、交易和存儲信息。他們正在計算,應該向你提供哪些信息,以及用什麼順序提供,使你的效用最大化(對他們來說,就像一個人類點擊農場human click farm)。他們正在製造界限。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哪裡應該有界線(提示:它看起來很像舊世界)。他們正在遊說,以摧毀他們在尋求統治、金錢和權力的過程中仍然需要行使的一點點克制。
而這一切的隱秘之處在於,新的建築師會讓你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新的世界,新的文化中,其實根本沒有什麼變化。新世界只是舊世界的反映,被扭曲、彎曲、變形。它有著有更多精心設計的敘事,在更多的媒介上延續。
我想在某種程度上,未來永遠無法真正擺脫過去。因為人類的知識是累積性的,一切新的東西都存在於舊的背景中。從人類歷史的這一點來看,我們的未來很可能再也無法忘記過去的任何東西,再也無法忘記。
但人類歷史的忠實性仍將受到質疑。
就像人類將信件保存了幾個世紀一樣,人和機器會囤積真相,並將其扭曲成自己慾望的形狀。

我們生活在一個由特定的規則和架構所定義的世界裡,隨著越來越多的東西被建立在現有的體系中,這個體系已經僵化了。要建立一個新的體系,我們不僅要用新的產品和服務,而且要用新的製度、新的政策、新的社會和文化價值觀來爭取擺脫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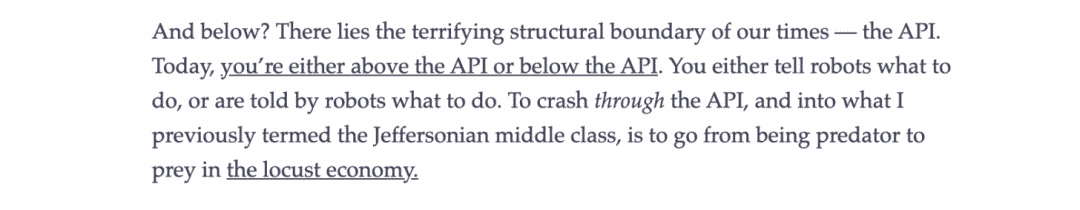
總的來說,我每個月想到Ribbonfarm的這篇文章,至少一次。它對我的衝擊很大。
正如Harold Bloom在《影響力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一書中所說,我們必須爭取擺脫前人的影響。過去的可能性決定了我們對未來的理解。
而這正是讓我夜不能寐的原因。這個世界的守門人,無論是老牌的、有錢的、政治精英,還是我們年輕的、無所不能的數字霸主,他們都有足夠的動力把我們擋在門外,甚至迫使我們相信,只要通過改變我們對未來的看法,我們就會加入他們的行列。而如果我們按照他們的藍圖來構建未來,最終的結果也是一樣的。
構建意義:比特幣的發展軌跡
當你朝著一個願景前進的時候,會發生這樣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創業者是創造現實畸變場的人。他們為一個不同版本現實描繪願景,如果他們能讓足夠多的人相信這個願景,並提供資本和影響力,那麼它可能真的會成為現實。在今天這個充滿影響力的時代,其實我認為創始人最重要的工作並不是基於技術或技能,而是他們能夠創造一個現實畸變場。這個畸變場非常強大,以至於每一個接觸到它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陷入同樣的畸變場中。
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比特幣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現在有數以百萬計的人生活在一個扭曲的現實中,在這個現實中,比特幣是一個全球性的價值存儲和金融網絡。對於那些歷史上被排斥的人來說,我們正處於復興之中,對於那些相信完全不同的東西的人以及對於那些被排除在未來設計之外的人來說,也是如此。現在的戰鬥是為了爭奪對那個未來的敘事權。
這就是為什麼華爾街巨鱷和小老百姓進軍比特幣是如此危險的原因,因為它會扭曲和改變我們對未來的看法,用一些淡化的東西來排擠我們最初的野心。擔負起責任的一代,守門人,他們必須讓新事物發生。這是一種自然的演變,但人們難免會反抗,因為這威脅到了他們的地位。對於新生代來說,面臨的挑戰是瘋狂的困惑——如何讓這場革命在不注水的情況下發生?
正如Karl Marx的名言,“我們假裝的東西決定了我們是什麼,所以對我們假裝的那一面要小心。”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假裝自己是革命者,這非常有趣,因為擁有一個敵人的感覺是最好的。
但現在,我們不再是革命者了,我們正在成為當權派。當所有人都在談論比特幣,然後Jamie Dimon說,“我錯了,比特幣太神奇了”,你就把比特幣存入他的金庫,沒有人再去戰鬥了,那我們還在努力什麼?
為未來而建設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未來看上去要與過去完全不同。我們必須建立新的建築、新的偶像、新的理想,來實現一個新的世界。
未來可能不會像過去那樣。
我們必須打破這些壁壘和孤島,才有可能實現這樣一個未來。這就是建築師的工作,建築師用科學、數學、設計和理性來建造橋樑,建造空間,建造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的過渡。
建築師用心使用工具。功能從形式中產生。
你渴望建造什麼,以及為誰建造,對於這些要小心。
你看,我們建造的東西會通過我們的體驗被表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