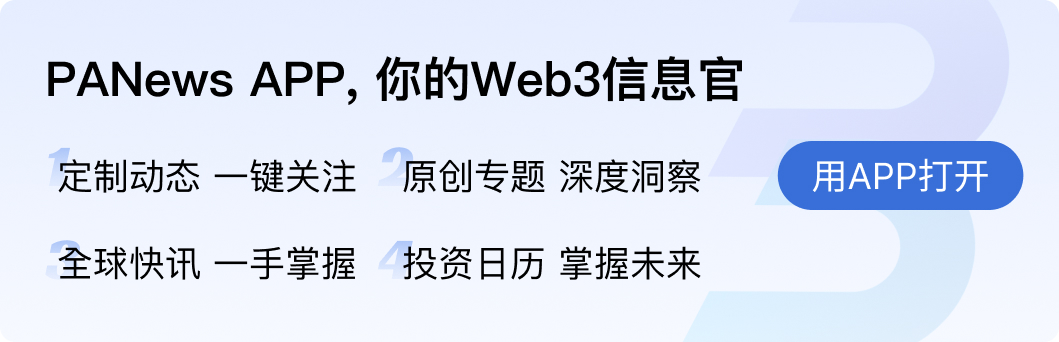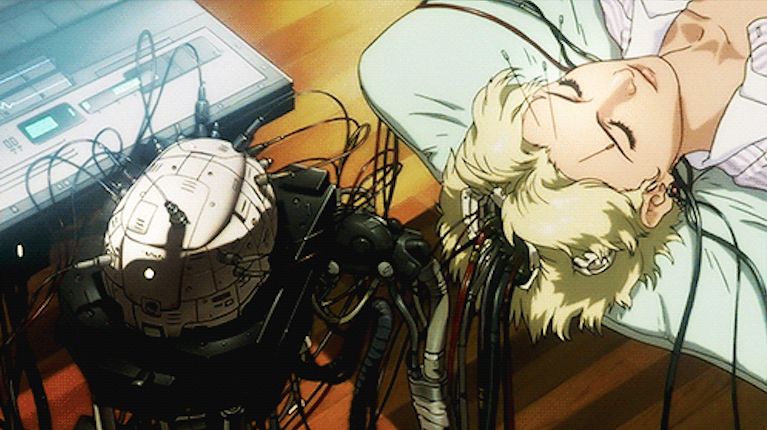
李陽約我給預言家週報寫一篇文章,不限主題,只要是自己的思考就行。最近關注的東西有些雜,但似乎又有一條隱形的線,也許寫這篇文章能夠幫助自己理清思緒。
柔性電極是一種比頭髮絲還細的電極,它與柔軟的腦組織相匹配,可以被長久地(這個特性很重要)植入大腦,並貼在神經元上(這個特性很重要)傳遞清晰的信息。柔性電極及其植入技術使得腦機接口不再是科幻,而是觸手可及的未來。 (在Neuralink的這個實驗中,小豬被植入了柔性電極,視頻中的聲音反應的就是它的鼻子接觸到了什麼: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LUWDLKAF1M)
腦機接口的未來,在科幻的世界裡是怎麼樣的?有兩個作品講了兩種極其悲觀的未來,分別是關於信息的讀出和信息的寫入的。
在信息的讀出上,是一本叫《量子竊賊》的小說,它是從一個糕點師的大腦私鑰被盜導致的意識失竊案開始的故事。如果我們無法對大腦的輸出加密,個體是間接被控制的,這也是我認為各種在不暴露數據的情況下實現數據可用性的技術是未來重要課題的原因。
在信息的寫入上,是黑鏡中《Men Against Fire》那一集,是一個輸入設備篡改了真實世界的故事。如果我們濫用大腦的寫入,個體是直接被控制的。允許什麼程度的信息寫入會是一個大大的選擇題,我們能否抵禦寫入的誘惑(巨大的誘惑、滑入其中的誘惑)不得而知。
腦機接口的未來,在現實的世界裡是怎麼樣的?它也許會把人類和人類社會更進一步、甚至全面地從物理世界推入數字世界。因為到那個時候,信息的最重要的、佔壓倒性優勢的載體將是數字,而不是其他任何選項。
關於「信息」的意義,諾伯特·維納有極富啟發性的見解,他認為:“任何有機體都是因為擁有獲取、使用、保存和傳播信息的手段才得以維繫和生存”。以及:“像個體一樣,社會系統是一個組織,它通過通信系統結合在一起”。
如果信息的載體是數字的而不是物理的,那麼不管是作為個體的人,還是作為組織的人類社會,無疑是生活在數字世界中的。
正在進入數字世界的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也許是秩序的缺失。人類的歷史也是一個秩序建立的歷史,我們有物理世界的秩序,但遠遠還沒有建立起數字世界中的新秩序。這其中最敏感的一個主題或許就是自由。在物理世界中,絕大多數個體知曉自由和自由的邊界、也有道德和法律來保護自由以及約束自由;但數字世界中,我們更容易看到兩個極端。
在一個極端,自由只存在於名義上。齊澤克講過一個蘇聯笑話:
“一個德國勞工在西伯利亞找到一份工作。他知道從那邊寫信回國,肯定逃不過審查官的法眼,於是跟朋友約定:如果我給你寫的信是用藍墨水寫的,就說明信上的一切都是真的;如果是用紅墨水寫的,那就是假的。一個月之後,朋友收到了他的來信,信是藍墨水寫的:這裡的一切都奇妙無比:商品琳瑯滿目,食物豐富多樣,公寓不僅寬敞,暖氣也很充足,電影院裡放的全是西方大片,還有很多漂亮女孩,可與她們眉來眼去。只是一樣不好:紅墨水缺貨。”
在另一個極端,是絕對的自由。但數字世界中,絕對的自由是可行的嗎?或者更現實的一個問題,「內容」應該是完全不受約束的嗎?這同樣是值得思考的。
比特幣、貨幣、賬本……它們抗審查沒有問題,這些信息不會傷害其他人;但內容是可能對其他人造成傷害的,傷害的對像不只是內容中涉及到的人,還有對看到這些內容的人造成的影響進而導致的實際上的某種傷害,比如藍鯨遊戲。
前種傷害也許可以通過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的身份的脫鉤而弱化,但後種傷害是難以避免的。當我們呼籲自由的時候,往往是從內容髮出者的角度,而忽視了內容的接收者。
但自由的邊界在哪裡,如何維持邊界,我不知道;但談論約束自由,是否就像在一個「me too」遠未被正視和解決的環境中談論《狩獵》,這種談論本身是否不恰當?我不知道。
與進入數字世界相關的另一個話題是博弈與合作,因為這個重要的議題或許也會因為數字化而發生變化,需要重新認識。
人是自私的,但人類的合作是可能的且重要的。一個重要的討論合作的可能性的實驗是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的「重複囚徒困境」遊戲,他邀請全世界最傑出的對策專家來設計策略進行重複囚徒困境博弈,這些對策專家來自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數學等等領域。
最後,遊戲的勝利者是所有策略中最簡單的一種:一報還一報。即如果對方在上一步背叛,自己在這一步就選擇背叛;如果對方在上一步合作,自己在這一步就選擇合作。羅伯特又邀請更多的人來設計策略,且這次的參與者知道上次獲勝的是一報還一報,他們可以針對該策略進行設計,但最後,獲得勝利的依然是一報還一報。
一報還一報揭示了基於回報的合作的可能性,但這種合作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合作的進化要求個體有足夠大的機會再次相遇,使得他們能形成在未來打交道的利害關係” (羅伯特)。
但在數字世界中,個體或組織是否有足夠大的機會再次相遇?未來打交道的利害關係和眼下的利益相比,是否重要?如果抽像一點,數字世界更多的是一個穩定環境的世界,還是一個變動環境的世界?
如果很少再次相遇或者不依賴於再次相遇,合作的一種重要前提條件沒有了,那麼數字世界的合作的可能性來自於哪兒,合作的形態會是什麼樣的?如果沒有合作,在物理世界中有效的行為方式或生存方式會如何改變?對於DeFi世界中的我們來說,不管是協議設計者,還是協議投資者,這些已經是現實的考量。
腦機接口的未來,在哲學的世界裡是怎麼樣的?腦機接口提供了一個好的條件,也許是前所未有的條件,讓我們思考人是什麼,以及思考機器/人工智能是什麼。
如果寫入信息、輸出信息都可以被取代,人剩下的是處理信息,它的處理的特別之處在於當我們根據輸入產生決策做出輸出後,會把輸出導致的結果再次輸入(反饋) ,而這個反饋將作為一個因素影響我們下一次的決策。
這個反饋過程也是人類克服熵增的工具。如果人類喪失了這個反饋過程,或許人是機器;如果機器實現了這個反饋過程,或許機器也是人。哈哈哈,這是我瞎想的。
此外,腦機接口弱化了肉體的重要性,也許離意識上傳脫離肉體還很遠,但至少人只需要維持頭部的活性即可,醫學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人就不會死;即便頭部維持技術一時半會兒未能實現,瀕臨死亡的人也可以選擇冷凍頭顱等待未來,相較於冷凍身體,冷凍頭顱的費用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可能是可承受的。
這也許意味著現存在世界上的人們,有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代「永生」的人,但死亡是哲學諸多命題的出發之處,沒有了死亡,哲學可能將是全新的議題、全新的內容。想想都很有趣,一個鴻蒙初闢的世界。
那麼就寫到這兒吧。這是一篇三腳貓一樣的文章,我對自己所寫的知之甚少;而且匆匆寫完未經周全的考慮,有什麼不當之處還請不吝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