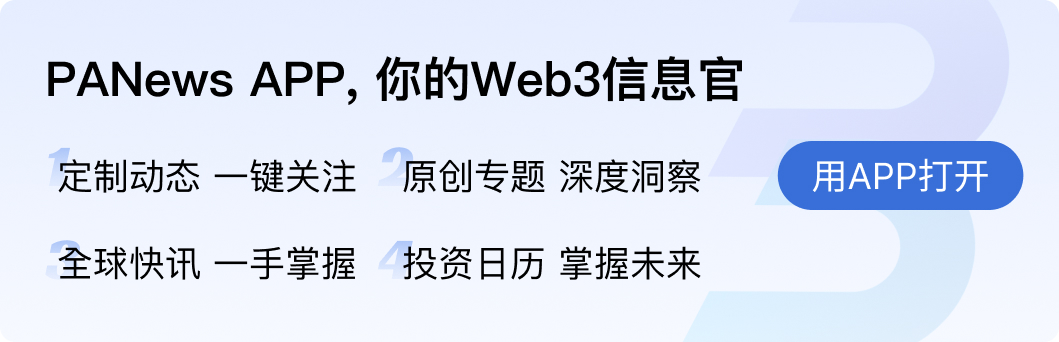01 引言
直播带货作为近年来的新兴网络事物,以其便捷性强、曝光率高、受众广的特点迅速成为各品牌商青睐的营销方式。在全民网络时代,除知名头部主播外,越来越多主体加入直播行业。随着主播群体日益壮大,行业“内卷”加剧,部分主播为获得更多带货量,在直播中过分夸大产品功效,甚至欺骗消费者。
而利用算法生成的虚拟主播AI主播的出现,为直播行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一定程度上吸引消费者关注,但其虚拟人设的特殊性也为其主体定性、法律规制、责任承担带来争议。例如,有人认为出现在某直播间的著名二次元人物洛天依推销某品牌口红违反了《广告法》关于“亲身试用”的规定。当AI主播进行直播带货,是否可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广告法》中对广告代言人的要求是否适用于AI主播?
02 AI主播直播带货的法律分析
(一)直播带货可能属于商业广告行为
长期以来,业界与学界对于直播带货行为的法律性质均存在争议,例如:直播带货属于商业广告还是商业宣传?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宣传乱象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规制力度更强的《广告法》?其争论的原因在于,由于直播带货内容并不当然地构成《广告法》中规定的商业广告;因而进一步讲,进行带货的主播并不当然地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
2020年11月6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对直播带货行为的法律定位进行界定,明确“直播带货的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应按照《广告法》规定履行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或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和义务”。该规定表明市场监管总局否定了直播带货行为不适用《广告法》的观点,但同时也认为直播带货不当然地全部接受《广告法》规制,避免过度管控。
具体而言,对于部分头部主播,消费者往往基于对主播的知名度与信任选择购买其所推销的产品,结合宣传语言、宣传效果,在某些情形下该类主播同一般广告代言人基本无异,应以《广告法》对主播进行规制;而对于为己方产品提供功能性介绍与推销的主播,其相比于线下商场售货员,仅通过网络打破时空限制,一般不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
纵观当下市场,虚拟主播AI主播亦可对应性地划分为两类:一是品牌商家自主定制的、“工具人”性质较强的数字人主播,其目标定位多为深夜时间直播,目的是降低用人成本、弥补真人主播无法做到24小时不断直播,该情形更类似于售货员线下推销,而非广告代言,不应受到《广告法》规制;二是品牌通过聘请第三方,使用著名IP形象进行直播带货活动,例如二次元人物形象洛天依,此情形下由于IP形象自带热度,粉丝效应明显,可收获类似于明星广告代言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从广告主体看,虚拟主播AI主播作为利用数字算法生成的虚拟形象,当然地不作为广告代言人。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广告代言人指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因此虚拟主播AI主播不应归属于现行《广告法》对广告代言人的规制范畴。
(二)虚拟主播AI主播直播带货的广告法风险
为呼应现实监管需要,已有多部法规或规范性文件针对虚拟主播AI主播提出行为要求。例如,《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第一条明确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的虚拟主播AI主播及内容,参照本行为规范”,将虚拟主播AI主播纳入与普通主播相同的法律地位,同样受到该规范规制管制;再如,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发布的《直播电商营销与售后服务规范》要求,直播使用的虚拟主播AI主播形象应符合公序良俗,应当提前对虚拟主播AI主播的脚本、动作等内容进行核验等。
此外,针对直播带货行为中可能被认定为商业广告的部分,《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已做有关广告法的专门提示,如第十四条规定,网络主播不得夸张宣传误导消费者、通过虚假承诺诱骗消费者、使用绝对化用语等;然而在《广告法》领域,关于虚拟主播AI主播,目前仍未专门作具体规定,相关监管部门亦未出台相关规范文件,但对于其中的普遍性的要求,可参照对一般主播的规定。
虚拟主播AI主播利用自身IP热度大力推荐某产品,吸引固有粉丝人群以及因“明星效应”而产生信任的其他消费者购买产品,此种营销行为及营销效果与一般真人广告代言无太大差异,例如将著名虚拟偶像洛天依引入直播间带来的粉丝效应收获显著带货成果。因此,即便虚拟主播AI主播的法律定位不属于广告代言人、不受《广告法》对代言人的规制,但有条件地部分适用《广告法》有利于规范虚拟主播AI主播的直播带货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例如,《广告法》规定了广告代言人的某些禁入领域,包括医疗、药品、医疗机械、保健食品;另外,《广告法》第三十八条要求广告代言人必须亲身试用过所推荐的产品。对于前者,考虑到特定领域安全性,可针对虚拟主播AI主播提出同等规制;而对于后者,则提醒数字人运营商应探索其他途径的产品审查方式,否则将存在虚假宣传的风险。
尽管虚拟主播AI主播不构成广告代言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用数字人进行直播带货就缺失管控,使其成为不受规制的“脱缰之马”。事实上,实践中已有案例表明,数字人主播介绍产品内容若存在散布虚假信息诱导购买,或者夸大功效、隐瞒缺陷等的情形,其仍应承担《广告法》规定的责任。此外,对于具有强大粉丝效应、营销效果与广告代言人基本无异的虚拟主播AI主播,当产品方、直播间运营者利用IP“偶像身份”,进行实质性广告代言宣传时,数字人运营者更应谨慎审查,若因未严格选品、未进行质量把关而造成直播“翻车”,不仅对数字人名誉形象及其经济价值造成损害,还有可能对产品损害责任、行政监管责任承担连带风险。
(三)虚拟主播AI主播直播带货的各方责任分配
《广告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前款规定以外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或者作推荐、证明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利用虚拟数字人进行直播带货,责任方包括直播平台、特定直播间运营者、产品品牌方、虚拟数字人运营方等众多主体。笔者认为,对应至《广告法》上述所提及的责任主体,以产品品牌方为广告主,直播平台以及直播间运营者为广告经营者,虚拟数字人运营方为广告发布者,在直播带货内容构成商业广告时,可以由上述各方可参照《广告法》的规定进行承担责任承担。
此外,与传统主播不同的是,虚拟主播AI主播不属于自然人,无独立人格与意志,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同时,由于虚拟主播AI主播属于算法生成,品牌与平台虽在对外宣传中强调虚拟主播AI主播的“虚拟”性,并以此凸显其科技色彩,但归结到主体意志层面,虚拟主播AI主播仍为其运营者所控制。数字人直播带货的背后,其选品、试用、宣传文案等均由直播平台或运营方完成,相应地,虚拟主播AI主播的虚假宣传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也应由其运营者承担,即提供数字人营销技术的公司。在传统直播带货关系中,主播所属的MCN机构对主播的违规行为也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相较对于此,在数字人自身无独立意志的情况下,其背后的运营机构更应承担较重的监管责任。
03 合规建议
如上文所述,同传统直播带货相比,虚拟主播AI主播直播带货涉及更多的主体。由于平台监管责任已在《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等文件中较明确地规定,因此本文将着重讨论数字人运营商在其所属的数字人被用于直播带货活动过程时的合规问题。
(一)建立严谨的产品选择机制
数字人主播以知名IP形象为产品背书,且可产生类似于广告代言的效果,但其实际上却无法亲身试用产品,亦无法亲自承担责任,正是此类情形构成了虚拟主播AI主播带货问题定性难的重要因素。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广告代言人是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形象对商品或服务作推荐证明的人,也即以自身的公众影响力与可信度为产品作背书。“亲身试用”即要求广告代言人严谨选择所推荐的产品,而由于数字人运营商为数字人的直接监管者,因此其应成为严谨选择产品的责任方。
尽管直播平台对所发布产品的选择有一定的事前审核责任,但构成广告代言效果的虚拟主播AI主播在产品营销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也获得不菲报酬。从权责相统一的角度看,虚拟数字人运营商在使用数字人形象进行直播推销前,应当与品牌方及时确认产品具体情况,与选品方核对各资质状况,并组建同公司相挂钩的产品试用团队,以公司名义对所属虚拟主播AI主播的“推荐”作背书。
(二)对直播过程进行技术监管
从具体直播内容看,数字人运营商可针对平台直播语言规范的要求,通过技术手段为成为虚拟主播AI主播的数字人设置合理合法、不违背公序良俗的言论;另外,对于可能被认定为商业广告的直播,应结合《广告法》第九条的要求规范宣传语言,如不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字样。
从直播全局过程看,相对于淘宝等传统网络购物方式,由于网络直播过程中宣传语言为口头发布,对于网络直播带货的事实过程难以完全复原,以致证据留存困难,不利于厘清各方责任。因此数字人运营商作为虚拟主播AI主播背后的第一责任人,应注意保存虚拟主播AI主播直播带货过程中运行产生的数据,可考虑采用适当的区块链存证平台进行存证,当发生违规行为或侵犯消费者权益时,通过该存证明确前述事故非由数字人自身技术缺陷而致。
04 结语
尽管已有文件明确规定部分直播带货可被认定为商业广告行为,但在现行《广告法》对广告代言人主体的规制下,由于非自然人身份,AI虚拟主播进行直播带货不能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
实际上,自带强大粉丝的知名数字人参与直播带货实际上能够产生事实上的具有广告代言效果,故而从市场监管及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看,应当对其加以类似广告代言人的责任,且真正责任承担主体应为数字人运营商。在初始兴起发展伊始、相关法规并不明确的情况下,数字人运营商应当明确参与数字营销的相关法律风险,在产品选择、运营监管等方面进行把控,同时关注行业法规的变更,以期尽可能减少自身的责任承担风险。
参考文献
-
刘双舟:《关于网红“直播带货”法律属性的思考》,载《中国市场监督研究》,2020年第5期,第21-23页。
-
刘晓菊:《“直播带货”参与主体的法律责任和风险防范》,兰州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
-
高悦:《数字人带货虚实:每月成本最低数百元,部分品类转化率远超真人主播》,2023-06-18,载凤凰网,https://finance.ifeng.com/c/8Qi0Le5HbF1
-
《直播带货领域,虚拟偶像如何立足?》,2020-10-23,载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网,https://www.woshipm.com/marketing/4224804.html
-
马辉:《社交网络时代影响力营销的广告法规制研究》,载《东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23期第1版,第32-40页。